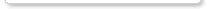21岁那年,此公就尝填“水调歌头”一阙曰:“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着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消磨。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直抒胸臆,发愿替苍生受苦,老百姓所受的苦其愿一人代受:胸怀济世到如此程度,委实是够可以的。
命中注定的“失败者”
尽管梁启超胸怀济世得真诚、坦荡,程度非同凡响,较之其顽固不化、一意孤行地认死理的老师康有为,也一直显得灵活机动、与时俱进,但是,从传统的“政治”意义的角度来说,他也到底是个失败者。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此后又游历欧洲。1919年10月,其时巴黎已是严冬季节,所谓“天地肃杀之气,已是到处弥漫”,隔窗望去,几片顽强的枯叶“还赖在那里挣他残命”。梁启超在巴黎附近白鲁威的公寓里,埋首把自己一年来游历欧洲的见闻与感想诉诸笔端,写成了《欧游心影录》。他满以为,自己这次充满感情的文字,可以匡正时弊,引导中国走上一条中西调剂的道路。但结果却并非如此。
向来以大开大阖著称的陈独秀,率先向梁启超发难。他反驳梁启超外科手术般的“改良主义”道路说,“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国政治的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革命),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revolution呢?”随即,主张“全盘西化”的钱玄同指责梁启超反对科学,甚为“荒谬”;就连向以“雅量”著称的胡适也批评他“谣言”惑众,“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了不少的威风”。三年之后,在声势浩大的“科玄论战”中,梁启超更被视为复辟封建传统的“玄学鬼”,成为胡适、陈独秀等五四一代的众矢之的。
这场论战,孰是孰非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但历史毕竟无法重演,四年后,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大革命爆发,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道路彻底失去了验证的机会。他这个最“抢戏”的“配角”,到底也仍然还只是个“配角”。
梁启超为什么会失败呢?很多年之后,有所谓“史学通人”之称的许倬云,在一本论及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者的书里,把梁启超放在了最后一个人物作为结尾,因为梁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中国最后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士大夫。他说,他之所以把梁启超放在结尾,就是要说明,中国士大夫的传统就是一直想要改革,一直想把理想带到世界来,但每个人所做的事情因为时代的限制,因为背景的限制,或是因为改革者自身性格的限制等,一路过来的改革人物几乎都是失败的。
在许倬云看来,梁启超的失败跟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所有改革者一样,都是有缘故的。因为,对一个组织或系统而言,任何变动都会牵动全体,整个组织和系统如此庞大,仅靠一小部分的变动来加以改革,是很困难的:修改一个小螺丝钉,一定会发生磨合的问题,所以改革成功的几率往往非常有限。较之改革者,“每个朝代的开创者,都是系统的设计者,等于是重新开始,负担比较少,而且往往鉴于前朝的困难与缺失,便进行一番全面的翻修。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唐朝末年到五代,因为军阀割据,国家分裂,所以宋朝就一百八十度转过来,将文官地位提高,武人地位压低。像这样全然的更动,往往会成功,因为不是只修补少部分,而是一概全换”。
笔端常带感情的青年楷模
据说,梁启超一生的各种著述多达一千四百万字,在将近三十六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他每年平均写作竟达三十九万字之多,委实勤奋得惊人,但他的这些“千金剑、万言策”,讲起来都是想要用政治来救国救民的,他到底一辈子也没有做到,如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不过,两相较之,时人乃至后人,似乎一直都更偏爱这个学生。其中,很大程度的原因可能在于,梁启超的性格天真、有人情味,不似康有为总板着一张“老师”面孔,而是笔端常带感情。据说,梁启超的书法无法跟康有为相提并论,但他的字出自张迁碑,拙而敦厚明澈见底,一如其人。
一位叫做夏德仪的老先生尝回忆说,彼时他住在苏北的乡下,交通并不方便,但每天有一艘船一个航班,带来梁启超主笔的《时事新报》,他和他的朋友们每天都在码头上等。从上海发行的话,四川一样有人在等。可见梁启超笔端之感情、之思想动人的程度。据说,梁启超尝有《俄罗斯革命之影响》一文,写于1905年,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所以,梁启超的朋友很多,文的有当时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武的有当时最好的战略家蒋百里。他后来要去旅行的时候,蒋百里丢下自己的职务就跟他跑,也有人贴了家财替他办政党。即使是后来群起围攻梁启超的陈独秀等青年一代,其实,早几年也都曾以梁启超为时代之楷模,并从他那里汲取过思想的营养来着。
关于梁启超的为人,颇有些很有意趣的故事。
譬如,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时间大约是在1926年3月,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而梁启超后来却公开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更好玩的一件“轶事”是,据说,蒋百里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启超落笔即文思泉涌,序成竟也多达五万字;梁启超觉得不好意思,想来想去就加写了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
还有一件事情也很有名。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但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还是答应出席证婚。不过,在婚礼上,作为证婚人的梁启超,竟然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以至徐志摩不得不哀求说,“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天涯有知己惜乎终无份
说起来,别看梁启超训徐、陆训得义正词严,其实,他自己也并非没有“出轨”过,至少“意识”上是“出”过了的。
那大约是1899年的事。那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没想到,“保皇”一事没办得怎样,却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事情据说大致是这样的:
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侨商有个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英文极好,因当天有西洋人参加宴会,便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席间,这位何小姐极为活跃,她的学识、谈吐,尤其是对梁启超著述的熟稔,使在座者都大感意外。整个宴会俨然成了何小姐与梁启超的“对语”。
席将罢时,何小姐忽然拿出一篇文章的原稿来给梁启超看,并说,这是她代梁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梁启超看了手稿既惊且喜:原来,梁启超刚到檀香山时,到处奔走演说;清廷驻檀香山领事馆买通了一家当地的英文报纸,不断写文章攻击梁启超。梁启超心中不服,但苦于不懂英文,不能回击,只好置之不理。不料此后不久,竟出现一桩怪事,另一家英文报纸上开始连载为梁启超辩护的文章,文字清丽、论说精辟,只是未署作者姓名。今日真相大白,原来那些为自己辩护的文章,竟都出自眼前这位华侨小姐之手。
临别时,何小姐还主动向梁索赐相片,得偿所愿后又投桃报李,回赠梁其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至此,梁怎样还不坠入情网?梁临返国,何前往送别时更直言,“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不要忘了小妹。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请来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惟有先生懂。”此言已近乎直接表白。可是,其时梁启超已有妻室,且曾与谭嗣同共创所谓“一夫一妻世界会”,尽管情欲翻腾,梁到底也怯于若自食其言恐招天下人耻笑,终惶惶挥别何蕙珍。据说,其时梁之状,有若逃奔。
事情还没完。
回国后,在理智上克制了自己的梁启超,内心深处的相思却已泛滥成灾,以至于连写了24首情诗,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其中有一首曰:“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这个“第一知己”,说的正是何蕙珍。
到底无法忍受之后,梁启超在一封写给结发妻子李惠仙的家书中,煞费苦心地讲述了自己对何蕙珍的态度,并表示,自己忍痛做出了“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不动声色地回信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就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李惠仙之所以敢这么说,其实是因为她知道,梁父是决不会同意梁娶小的。夫人此举让梁启超着了慌,他急忙复信,求妻子手下留情,信中如此惶急地写道:“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馀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至此,梁启超才最终“死”了自己的那份心。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里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后,何蕙珍也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姿态固然做得极好,但如此做法却多少显得薄情了一些,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后来也要责备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这样说起来,梁启超的一生,未免有些“事业”、“爱情”双失意的样子,凄凄惨惨得很,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当然也不尽然。
譬如,对于现代中国的启蒙而言,梁启超就绝对是一个“成功者”。或者可以这么说,就是,没有梁启超,就没有启蒙,没有梁启超,后来的中国就是另一个样子。用后来的学者周善培的说法是,“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是被梁启超的一支笔“惊醒”的:他的笔,从法律、政治到经济,到诗歌到戏曲,无一不通,政治上虽然没有如愿,思想上却成功“推动”了后来的整个中国。他的“胸怀”诚然是真的“济世”了的,只是跟他自己设想的方式多少有些出入而已。
1929年,梁启超病逝,但却留下了很多有用的人,继续做着“胸怀济世”的事。有的是朋友,当然也有的是“敌人”,还有就是,其人“龙生九子”,竟然几乎个个杰出:长女梁思顺,后为诗词研究专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长子梁思成,后为著名建筑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娶妻林徽音;次子梁思永,著名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三子梁思忠,因病早殇;次女梁思庄,后为著名图书馆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四子梁思达,后为著名经济学家;三女梁思懿,学生时即曾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骨干,后为著名社会活动家;四女梁思宁,受其姐影响,早年即投奔新四军参加革命,后蒙冤退隐;五子梁思礼,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